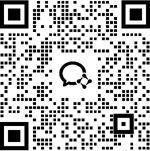“宣威火腿天下香”。宣威火腿以它矫健的步伐跨出了国门,让老外也竖起了大拇指。而一直与之相伴的豆面汤,却是养在深闺人未识。如小家碧玉一般素静美好,有一种你记得或不记得我都在这里的淡然。这里说的豆面汤,其实就是乌蒙山里特有的干酸菜和豆面条的联姻,二者缺一不可。

想起豆面汤,便想起很多年前母亲在昏黄的灯下擀面的场景是那样的温馨。那时父亲在外工作,农忙时的点种,母亲只有请周围的邻居帮忙。而点种的前一天,母亲便会把豆面条擀制出来,以备待客之用。乌蒙人家,一碗豆面汤,一碗砂锅炖出来的老火腿,在加几个小菜,一壶自家酿的苞谷酒,便是乌蒙山里人的待客之道了。

擀面的程序不是很复杂,但却费时费力。吃过晚饭,母亲打理完家务,便取出用土漆漆得光影可鉴的擀面棒和面板洗干净,提出装豆面和麦面的白布袋子,按一定的比例把豆面和麦面舀入盆里,放入水和一点点盐,当把面团揉得筋道有弹性,用手指一按一个窝,那窝又能慢慢长平的时候就可以放到面板上了。这个时候的面团要做到三不粘:不粘手、不粘盆,不粘刀。
看着母亲轻巧的手在面团上抚弄着,面团由不大的面块慢慢变大,最后一次从擀面棒上打开来的时候,那又大又圆的面皮总让我吃惊,打心眼里佩服母亲,想着长大以后一定也要向母亲一样擀出又大又圆的面皮。母亲把直径一米多,厚不到两毫米的面皮折叠起来,用刀切成细细的丝,提着最上面一层轻轻地一抖,那金丝一样的豆面条就像变戏法一样在母亲手中晃荡开来。我坐在旁边,母亲总会切一块面皮放到火钳上让我抬着烤得焦黄,那烤面皮的香味一直飘在二十多年后今天我的嗅觉里。

有了豆面条,还得说一下这干酸菜。干酸菜是晚秋时节,自家地里种的大白菜(有的人家也用青菜),选一个天高气爽、艳阳高照的日子,把大白菜成排的放倒在地里,让太阳晒的绵软之后(又杀菌又便于清洗不至揉碎),背回家一颗颗的洗干净,放入开水中焯一下,捞出趁热放进瓦缸里按紧实。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就能闻到酸味儿,那颜色还是碧绿碧绿的,就可以晾晒了。
豆面汤的做法很简单,水开之后,放入酸菜、姜、蒜、盐,三至五分钟放入面条煮熟就可食用,汤清面白,撒上一点点香菜,配一块红红的卤腐,酸中微有一点点豆面的甜味,这样的一碗豆面汤一直让我心仪至今。这是素吃。再就是把酸菜用油炸黄煮出汁水,依个人口味放进佐料。面条煮熟倒入味汁里面拌匀,放上葱丝,淋上少许红油即可。那炸黄了酸菜的浓浓香味总是要让人稀里呼噜忙忙的吃上几大口,才能慢下来细细品尝。豆面汤解暑,开胃消食,提神健脑。酸菜、大豆、小麦是乌蒙山里土生土长,原汁原味的纯绿色食品。滇东北的这片土地上,气候适宜,特别是有沙质土壤的。

地方是适合黄豆生长的。黄豆的营养毫不逊于牛奶,被称为“田中之肉”。很多的营养成分是其他作物不能比的。对于山里长大的我们,从小就没见到过牛奶、钙片,但一个个也是身强体壮,健健康康的。这都是老祖先们智慧的结果。乌蒙山里的人们,刨在土里,吃在土里,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,生活的艰辛自不必说。但他们却用他们的勤劳和智慧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,让从乌蒙山里走出去的游子忘不了儿时家乡的味道,忘不了儿时母亲做的豆面汤的味道,更忘不了母亲擀面时额头渗出细微汗珠的脸庞。豆面汤,这个“汤”是乌蒙山里人谦逊的叫法,有客人的时候,他们把肉类叫菜,其他的小菜他们都管叫汤,他们总是对客人说,不成敬意没有什么菜招待你,其实已经是满满一桌子的菜了。(袁 青)